想進行雙語教育,必須了解兒童獲得語言能力的奧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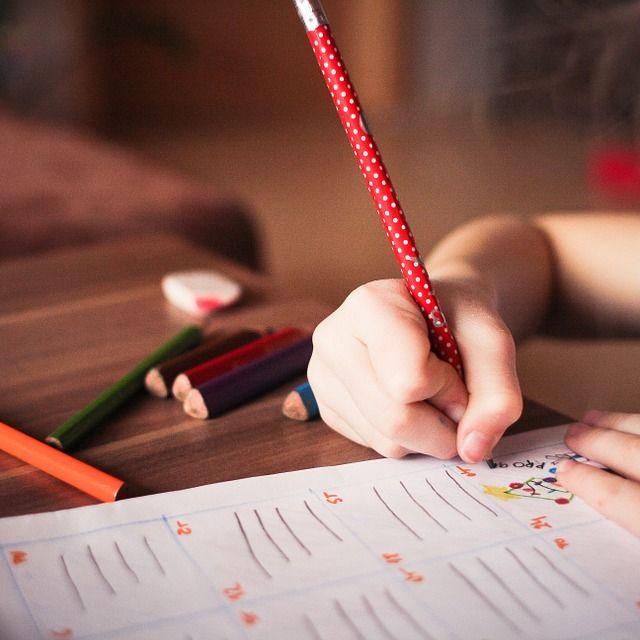
 麥圈媽媽在加拿大,卡爾加里大學兒童雙語在讀博士
麥圈媽媽在加拿大,卡爾加里大學兒童雙語在讀博士
Steven Pinker 曾經言簡意賅的說過一句話:“I have never met a person who is not interested in language.”
我細心回憶,還真是這樣,我也從來沒碰到過一個對說話,這一人類獨有技術不感樂趣的人。從有了孩子之后,我熟悉了良多優異的怙恃,他們在兒童說話教育方面支出的心血之多讓人贊嘆,這里面既有雙語怙恃也有單語怙恃。所以我完全可以稍稍改動一下 Pinker 傳授的話:“I have seldom met a parent who is not interested in raising a bilingual child.”
在兒童早教范疇,說話不僅僅是讓兒童可以把握指著某物說出名稱的使命,也不僅僅是可以讓特朗普的孫女背誦出《三字經》,或者讓一個雙語幼兒園的小伴侶會唱 Old Macdonald Had a Farm。說話對兒童的意義比這些重大得多了。
它可以幫忙兒童調節情感:當一個孩子能說出“害怕”,“生氣”的時辰,他學會了用說話安撫本身的情感,在說出來的時辰他就已經獲得了撫慰。它可以幫忙兒童紓解暴力行為:當一個孩子能說出“別動我的工具”“我不喜好你接近我”“媽媽你別走”的時辰,他原本可能會推,咬,痛哭的行為就用說話進行了轉化。
所以,要領會雙語是什么,就必需領會說話是什么,以及兒童是若何獲得說話能力的。學界今朝公認的方式是概率法,請列位怙恃細心閱讀。
剛出生時腦筋一片空白的嬰兒,大腦要領受其它人類的各類各樣的詞語和句子,好比媽媽會說“寶寶,媽媽愛你”,爸爸會說“讓爸爸抱抱”,然后幾個月或者一段合理的時候之后,嬰兒會迷糊地朝著媽媽發 mama,朝著爸爸發 baba,到一歲之后,嬰兒們根基上城市看到媽媽就很清楚的發 mama 這個音,看到爸爸發 baba 這個音。
聽起來很簡單,但細心想想真的太不簡單了:經由過程聆聽大人的語句,嬰兒怎么知道媽媽這個女人的稱號就是 mama,而不是“媽愛”或者“寶媽”?而爸爸這個漢子的稱號就是 baba,而不是“讓爸”或者“爸抱”?究竟結果,這兩個詞一般不是孤立的,絕大大都是和其他聲音詞匯在句子里呈現的。
也就是說,這些小腦殼瓜是怎么知道爸爸,媽媽是一個詞,而寶寶,抱抱,讓,愛你,又是其他的詞的呢?
1996 年,在 Science 上頒發了題為 Statistical learning by 8-month-old infants 的一篇重磅論文,這篇論文經由過程對 8 個月大的嬰兒進行嘗試,用科學的實證方式告訴我們,嬰兒本來是用概率方式來作出這種判定的。
讓我來本身用一個簡單的例子詮釋一下:好比 blue 這個詞,媽媽會說 blue car,或者 blue sky,又或者 blue eyes 等等。久而久之,這樣的詞語堆集多了,嬰兒聽在耳朵里,大腦會主動統計:“啊!本來 /blu:/ 在一路呈現了 10 次,/lu:ka:/ 在一路才呈現了 1 次喔,所以 blue 是一個自力的單詞,而 luecar 不是一個自力的單詞!”
嬰兒就是這樣,依靠于音節呈現的組合頻率(frenquency)來進行單詞朋分的(word segmentation)的。
在精確得知 blue 是一個零丁的單詞之后,嬰兒下一步的使命是再次經由過程概率方式,精確知道 blue 是什么意思。我們來繼續舉例子:第一天,爸爸擺好一藍一黃兩個小汽車,說 blue,yellow!第二天,爸爸擺好一藍一黑兩個小積木,說 blue,black!第三天,爸爸擺好一藍一白兩個小橡皮鴨子,說 blue,white!多次頻頻之后,嬰兒就大白了,藍色的汽車,積木,橡皮鴨子是 blue 的。因為,blue 這個單詞和藍色的工具一路呈現的概率是 100%的,而其他物體不是。
這就是嬰兒進修母語的概率習得方式,也是今朝為止被科學嘗試普遍認證的方式。
給大師詮釋嬰兒進修母語的奧秘,對兒童的雙語習得,甚至是二語習得都意義深遠。因為無論是怙恃,學者,仍是進修者自己,我們所有人窮盡一切盡力和研究的最終目標,無非是讓我們的外語把握水平能無限接近母語的把握水平。
所以,若是要讓一個雙語兒童真正當作為把兩種說話像母語一樣去運用和表達的人,那么最科學的方式就是模擬人類習得母語的方式。
是以,對 6 歲以下的孩子來說,最好的雙語進修模式就是經由過程大量的聽,培育語感,來讓兒童本身經由過程這樣的概率方式或者其他學界尚未詮釋清晰的方式,去天然而然的習得雙語。而這不單是最合適母語習得法的體例,也幾乎是獨一的體例:因為 6 歲以下兒童的認知和心理能力還達不到用學術的方式來紀律進修說話的高度(也就是我們說的顯性進修機制)。
- 發表于 2019-04-29 21:14
- 閱讀 ( 801 )
- 分類:其他類型
你可能感興趣的文章
- 怎樣在QQ空間農場中將普通攤位升級到第5級 883 瀏覽
- 谷歌瀏覽器怎么刪除某個cookie 933 瀏覽
- 女性40以后飲酒對身體的影響 840 瀏覽
- 如何對Word中的表格數據快速求均值 885 瀏覽
- 在PPT中讓文字逐條顯現 827 瀏覽
- p使用pr的小技巧-2 781 瀏覽
- Office2013官方正式版免費完整下載安裝激活教程 818 瀏覽
- 吃完大蒜嘴里有味兒怎么辦怎樣去除口臭味兒 1064 瀏覽
- PR 做一個黑白世界的效果 977 瀏覽
- 怎么查看Delphi軟件中控件的屬性及代碼 831 瀏覽
- 如何查看電腦處理器(CPU)的詳細參數 1058 瀏覽
- 吃西葫蘆對你身體有哪些好處 837 瀏覽
- photoshop使用內容識別刪除選中區域 1271 瀏覽
- 如何快速找出excel兩列數據的不同項 1161 瀏覽
- win8系統如何禁止特定指定軟件程序聯網 988 瀏覽
- MATLAB畫圖標記特殊點的方法 2243 瀏覽
- 圖解利用WPF創建一個全屏應用程序 775 瀏覽
- Excel技巧之——去掉數據透視表中的“空白” 3081 瀏覽
- 采用MATLAB畫一個分段函數圖像的方法 1205 瀏覽
- word中輸入某個字后顯示的是其他內容該怎么辦 1108 瀏覽
- chemoffice 2018 如何激活 1341 瀏覽
- 如何從百度云上下載視頻到電腦中 999 瀏覽
- WPS怎么給表格行添加背景色 1055 瀏覽
- Word如何設置編輯內容 969 瀏覽
- BIOS退不出怎么辦 1669 瀏覽
- WPS怎么插入表格 1140 瀏覽
- word插入圖片后只顯示空白框該怎么辦 2617 瀏覽
- 房天下上怎么設置消息提醒 959 瀏覽
- IE瀏覽器版本號怎么看 990 瀏覽
- 房天下怎么進行字體切換 867 瀏覽
相關問題
0 條評論
0 篇文章
作家榜 ?
-
 xiaonan123
189 文章
xiaonan123
189 文章
-
 湯依妹兒
97 文章
湯依妹兒
97 文章
-
 luogf229
46 文章
luogf229
46 文章
-
 jy02406749
45 文章
jy02406749
45 文章
-
 小凡
34 文章
小凡
34 文章
-
 Daisy萌
32 文章
Daisy萌
32 文章
-
 我的QQ3117863681
24 文章
我的QQ3117863681
24 文章
-
 華志健
23 文章
華志健
23 文章
推薦文章
- 怎樣才能拍攝出好看的婚紗照
- 新生兒姓名重復人數怎么查詢
- 微信怎么解除綁定的手機號碼
- 攜程上怎么領取優惠券
- 微信賬號如何進行申述找回
- 微信怎么制作電子名片
- 微信里的音頻文件怎么收藏保存
- 如何查看微信賬單
- 微信聽筒模式如何切換回來
- 怎么在微信里查詢社保信息
- 微信怎么把收藏的內容分享到朋友圈
- 斗魚直播怎么聯系客服
- 微信怎么設置不讓別人加自己
- 微信里的聊天記錄如何打包發給別人
- 怎么更換微信綁定的手機號
- 美顏相機怎么去除水印
- 王者榮耀如何讓別人看不到戰績
- 微信如何查看實名認證信息
- 手機阿里巴巴怎樣使用以圖找貨功能
- 微信保存的圖片在哪個文件夾里
- 華為手機計時器功能怎么使用
- 快手上怎么賣東西
- 蘋果手機自動刪除軟件怎么辦
- 怎樣最低的價格買到心儀的手機
- 蘋果xsmax怎么設置動態壁紙
- 百度手機衛士如何關閉軟件鎖
- iphoneX屏幕怎么分辨原裝
- 微信如何設置支付時驗證身份
- 微信聊天聯系人為什么多了耳朵標志?如何關閉
- 微信支付如何設置親情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