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心理學的人,是真會養孩子啊
 學心理學的人養小孩會有什么分歧嗎?
學心理學的人養小孩會有什么分歧嗎?
 胡立,心理咨詢師。咨詢請值乎,線下咨詢坐標杭州。
胡立,心理咨詢師。咨詢請值乎,線下咨詢坐標杭州。
好比說我們家會出格尊敬熊孩子的自立決議計劃權。
所以,熊孩子擺布腳鞋子反穿,好天穿雨鞋,炎天穿棉鞋,冬天穿涼拖,短褲配棉襖,短袖搭棉褲,等等各類騷操作,我們都隨他去了。

因為我們始終堅信生命本能的設計不會讓他出多大的差錯:
什么時辰該穿什么,得他本身去體驗、去感觸感染了,從而做出合理的判定和決議計劃,而不是麻木地執行由我們輸入給他的指令。
我們對他獨一的要求就是:本身的選擇本身負責。
我會告訴你準確的、最適宜當下天氣情況的穿法是什么,可是你有本身決議穿什么的自由。
但你如果冷,我可不會脫了本身的衣服給你保暖。你如果炎天穿棉鞋感覺熱,那你就脫了棉鞋本身打光腳!
不外,他這潮水穿搭我們看得下去,被大爺大媽們可看不下去 :
有人會好心的提醒,有人則是在旁邊哂笑,一臉“這孩子怕不是個智障吧”的關愛臉色。(手動捂臉? ??)
這也算是從小就糊口在非議傍邊吧,哈哈
再好比說很多家長一看見水池水坑,就趕緊帶著孩子繞道走。
甚至是哄騙打單孩子,水池里有這樣那樣的怪物,玩了水會有這樣那樣恐怖的后果。
其一是擔憂孩子弄濕弄臟衣服或弄臟房間,給本身找麻煩。
其二是擔憂孩子玩水會生病傷風。
其三是擔憂孩子的平安。
可我是怎么做的呢?
1、專門給熊孩子買了雨鞋去踩水坑。
2、專門給熊孩子端盆水,拿上各類玩具到門口去玩兒水。
3、只要不是會危及生命平安的水池深度,就隨便玩兒。
4、即使是水深的河濱,不是不讓他去,而是在背后綁根繩索,而且提醒他注重平安。既可以或許讓他去摸索平安鴻溝,又不會真的發生平安變亂。

就我這種自由摸索鴻溝的教化體例吧,直接導致了熊孩子在兩歲那一年失落進我們小區的水池七次!(水深及熊孩子的腰部以下)

不外,我這種帶娃體例也把一眾帶娃的白叟們嚇得夠嗆。
甚至有白叟出于公理感和責任感,對著我破口大罵。估摸著他們是對此刻的年青人帶孩子這么心大無比地憤慨吧。
唉,忍了,忍了。
人家也是出于好意,關心孩子,我能腫么辦嘛。
不外呢,可能正因為這種頻仍失落水池的經驗,直接成果是我家熊孩子對平安鴻溝把握得出格好,什么處所可能有危險,他本身門兒清。
底子不消我說,本身就會本家兒動回避失落。帶起他來出格地省心。
而且,均衡感也出格地強。
而這些,都是失落水池失落出來的經驗呀。

一、從不要求孩子聽話。
良多家長城市憂?于孩子不聽本身的話的問題,但我們家就完全不存在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底子就不要求孩子聽話。
熊孩子出生到此刻四年半了,至少在我和師長教師這里他從來沒有聽到過“聽話”這兩個字。
事實上,家長對孩子聽話的要求,源于家長對孩子的掌控欲:
你馴服我的小我意志,我就獎賞你;
你不馴服我的小我意志,我就從操行上否認你!
把“聽話”當做判定孩子操行黑白的硬指標,是最高效地辦理孩子、讓孩子從命的手段,但也是最高效地扼殺孩子自力思慮能力的東西。
所以,在我們家除非是告急環境,我們可能會利用強制手段。其它時辰,絕大大都的不合,我們都是用溝通來解決。
不外是多花點時候、精神和耐煩嘛,可是這樣的破費我相信對孩子的當作長來說,比支出金錢更有價值。
因為,我但愿他當作為一個自力的“人”,而不是一個思惟奴隸。
二、從不棍騙糊弄他。
良多時辰家長們對孩子使出哄騙的手段,無非是想投其所好或者使其驚駭,以快速達到讓孩子馴服本身指令的目標:
不讓他玩水,就哄騙他水下有鬼魅。
不讓他玩火,就哄騙他晚上要尿床。
不讓他吹口哨,就哄騙他晚上小偷會來偷工具。
不讓他玩雨傘,就哄騙他玩雨傘了會長不高。
可是,我們在用假話哄騙孩子的時辰,同時也在用假話構建他對客不雅宿世界的認知。
也就是說,我們知道是假的,但孩子不知道,他會信覺得真。他的心里里會對這個宿世界發生很多不需要的驚駭和擔憂。
當他長大了,有一天醒悟過來,也會對這些棍騙感應憤恚。
更主要的是,他的思維和認知體例會發生扭曲,他會像這些假話一樣對客不雅事物成立錯誤的因果聯系。這才是假話對孩子最大的風險。
所以,我們在絕大大都環境下都對他真話實說。
好比說他有段時候天天晚上幼兒園下學回來,居心去衣柜里把衣服翻出來,一會兒換一套,一會兒換一套。
那我就會直接和他講:
固然你有自立選擇穿什么衣服的自由,可是也請在行駛本身的自由選擇權的時辰考慮一下他人。
你換這么多衣服,我又要洗又要晾又要收,我很辛勞的。要么這些活兒你全數本身干,要么你就得稍微禁止一下。
三、教育過程中長于自我反省。
舉個栗子:
前兩天,我發了一條伴侶圈,吐槽熊孩子一個單詞教了很多遍仍是記不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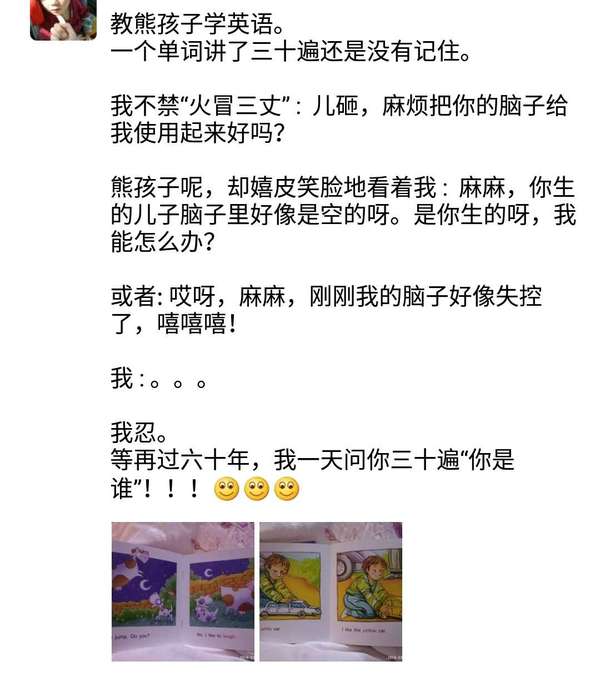
不外呢,吐槽歸吐槽。
事后我就會總結反省:
對于一個智力發育正常的孩子,若是一個單詞教幾十遍都記不住,那就不是學的人的問題,而是教的人的問題了。
良多時辰,當我發現熊孩子沒有按照我所期望的那么做的時辰,我就會自我反省:
問題的癥結到底在哪里?
是我對他的期望太高他的能力成長還不到位,仍是我的方式出了問題?
總之并不是一味地把責任推卸到孩子身上:
出了問題都是孩子的錯,孩子懶,孩子笨,孩子不當真,本身一點問題都沒有,那對孩子就太不公允了。
就像是那些吐槽陪孩子寫功課心臟病發的家長,其實大多應該做的是自我反省,而不是求全譴責孩子。
四、因材施教。
耶魯大學曾遴選一群一歲擺布的嬰兒做過一個心理學試驗:
在使命歷程受阻的時辰,那些更多表示得脾氣安然平靜的寶寶很快就拋卻了繼續測驗考試;
而那些更多表示出憤慨情感的寶寶卻不那么輕易拋卻,他們對峙測驗考試使命的次數遠遠高于脾氣安然平靜的寶寶。
以此證實,憤慨情感是有助于人類保存的順應性行為。
不外呢,我家熊孩子是一個典型的脾氣安然平靜的寶寶。
所以他很是地消極灰心,老是等閑地拋卻繼續測驗考試,也很是害怕面臨掉敗。
好比說,我們去趕公交,面前著時候來不及了,我就催他:加油,還有三分鐘!
他卻一屁股坐下了:嗚嗚,必定來不及了!
好比說,玩游戲的時辰,他若是感覺本身碰到了堅苦,或者感覺本身贏不了,他就會間斷游戲,因為他心里害怕掉敗的成果。
正我們因為領會他的個性特點,所以我們就會針對性采納一些手段來讓他在繼續連結脾氣安然平靜的環境下,可以或許加倍勇敢地測驗考試,不輕言拋卻:
1、讓他發現,只要不拋卻,就有可能當作功做到的正標的目的激勵。
2、即使對峙盡力仍是掉敗了,可是這并不代表我們就垮臺了,還可以測驗考試其它方式解決這個問題。
例如,錯過了這一趟公交車就尋找另一趟同樣可以抵達目標地的公交車。
3、示范給他看,即使掉敗了,我們仍然會繼續測驗考試,一次又一次地總結經驗教訓,繼續挑戰。
例若有一些益智類或者技巧類的玩具我玩也會碰到堅苦。于是,我就借這個機遇示范給他看,我是怎么一次又一次不拋卻地尋找方式解決問題的。
此刻,我已經經常能聽到,他本身玩玩具碰到堅苦的時辰在嘴里念念有詞:我不拋卻盡力,我會繼續對峙測驗考試的!
五、碰到問題,教孩子應對,而不是回避、掉控或撕逼。
近幾年,很多諸如批判惡作劇把玩簸弄小孩兒的爽文在收集上爆紅。
可能是曩昔國人的自我在集體本家兒義文化里被壓制綁縛得太久,此刻那些曩昔被壓制的人們走到了另一個極端,覺得自由就是無所忌憚地釋放本身的自我:
只要我是公理的一方,我就應該要以公理的名義撕逼、絕交。
所以,我在知乎上回覆示范我若何教孩子應對伴侶對孩子的打趣和把玩簸弄的時辰,下面一大片評論攻訐我:
不負責任,不知道庇護本身的孩子,居然交友這樣的伴侶,居然不和伴侶翻臉等等等等。
可事實是,人類幾乎所有的打趣都是針對弱者的,這是遍及存在的客不雅事實。
而且,伴侶逗弄孩子,更可能是他不知道應該怎么和孩子互動。固然他這件事做得不合錯誤,也不代表就可以以此否心猿意馬他的全數。
別的,也沒有誰可以或許擁有十全十美,一點都不會讓本身不舒暢的伴侶。
所以,我們一向給熊孩子培育的一個理念就是:
挫折、挫敗、危險、心理上的不舒暢,這些在實際宿世界往往都無法完全避免。不本家兒動找罪受,但更主要的是,堅苦來了,我們要知道若何應對。
作為小我,我們能力有限,無法改變他人,改變宿世界,可是我們可以改變本身應對堅苦的方式。
由此,我們引申到下一個常識點:積極應對與消極應對。
六、積極應對與消極應對。
有一天晚上,熊孩子拎著一袋子玩具去小區草坪上玩。
熊孩子出格高興地拿著玩具處處嘚瑟。成果就被幾個大孩子搶玩具,而且最后也沒有送回來,順手一丟就走了。
回來的路上,熊爹就罵他:
今后禁絕再拿著本身的玩具處處嘚瑟!
而且,若是你本身不克不及庇護本身的玩具,那么今后就不要把你的玩具給我帶下來!
要說熊爹也是心疼熊孩子,可這樣的處置體例其成果是會把孩子隔斷在這個真實宿世界之外,因為“孩子們一路玩游戲”是兒童成立友情、成立社交關系的本家兒要手段。
而且,這句話是在徹底地否認熊孩子庇護本身的能力,會對孩子的自傲心造當作沖擊。
所以,這樣“動不動就我不和你玩了”的消極應對體例不成取。
所以,我趕緊解救:
不妨,今后玩具仍是可以帶下來玩的。
不外,帶下來就要記得庇護好它們喲。否則,到時辰人家搶你的玩具,或者把玩具丟獲得處都是,你心里也不高興啊。
今后再帶玩具下來給其他小伴侶玩要記得先聲名端方:
這是我的玩具,要玩我的玩具要顛末我的許可,不成以搶我的玩具。玩好了請幫我放回這里來,不成以處處亂丟!
還有,你還小,面臨那些年老哥的時辰不知道怎么應對他們,這是很正常的。若是下一次再碰著這種環境,可以標的目的爸爸媽媽乞助哦!
所以,消極應對和積極應對的區別就是,一種體例會把孩子鎖死在一個小圈子里,而另一種體例,則是不竭地鼓動勉勵孩子標的目的外探尋。
窮年累月下來,就會形當作天地之別的差別。
七、不僅僅是常識點,還有邏輯關系闡發。
良多家長都知道讓孩子擁有豐碩的常識儲蓄對孩子當作長的主要性,可是良多家長不知道把這些常識點串起來,理清客不雅事物的邏輯關系對孩子當作長的主要性。
其實,無數海量的數據存儲在腦子里,卻不知道他們之間的邏輯關系,甚至他們之間成立了錯誤的毗連,不知道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不知道若何運用。
那么,這些數據都只是冗余信息罷了,沒多大用處。
而我們在考量一小我的智商時,很主要的一點叫做“抽象思維能力”。
那考查的不是一小我記住了幾多常識,而是看這小我能不克不及用抽象的概念進行邏輯推理演繹。
舉個栗子:
有一次,我和熊孩子坐在公交車上,有一架戰斗機從頭頂上飛過。
公交車開過幾個站后,我們還能看到這架戰斗機。
熊孩子出格高興地對我說:媽媽媽媽,快看,這架戰斗機跟著我們走誒。
可能很多家長碰到這種環境也就是擁護一下了事:是的呢,這架戰斗機真的在跟著我們走誒。
孩子一旦獲得這樣簡直認,他就會信覺得真。但其實他獲得的是錯誤信息,成立的是錯誤認知。
所以我對熊孩子的回覆是:
這架戰斗機只是看起來是在跟著我們走。
其實,只是剛好它的航標的目的和我們的公交車行駛的偏向一致,而且因為它距離我們很遠,所以看起來相對位移連結了不變,使我們誤覺得它在跟著我們走罷了。
(當然,在這里要提醒大師,對兒童思維能力的練習不要急于求當作。低齡段兒童大多處于動作思維和形象思維階段,要尊敬孩子思維能力發育的天然紀律,不要對孩子發生過高的等候。)
八、我們做錯了也會標的目的他報歉。
我們但愿可以或許用現實步履告訴他 :
不完美的宿世界里,是不完美的你,不完美的我們,以及他們。
你不是完美的孩子,我們可以理解。
可是,我們也不是完美的怙恃,也請你可以或許理解。
而我們作為通俗人,人人都可能會犯錯,但主要的是不再重蹈覆轍,而且知錯能改。
因為,若是我們作為怙恃若是從始至終都不認可本身有錯,這會讓孩子發生對怙恃完美化的等候。
而且,一旦未來他發現我們也犯了很多糊涂,做錯了很多工作,他們的認知就會解體,無法接管實際,造當作認知掉調。
而這,也是童年暗影和原生家庭問題形當作的本家兒要原因。
限于篇幅的關系,這里就分享這么多了。
究竟結果數一數都 4000 多字了,我怕是良多伴侶都沒有看到這里都封閉了這個頁面了吧,哈哈。
最后想說,固然我做到了良多可能對孩子當作長有益的工作,可是我并不確定最終會把他培育當作什么樣。
或許,更客不雅地對待宿世事萬物,更不變的情感,這個我仍是比力有決定信念的。
可是,因為我和師長教師兩小我都是死宅,而且都是懶癌晚期患者,而且,我們還持久地在養育孩子過程中執行一種叫做“天真爛漫”的策略。
所以,他可能比常人更懶散,更佛系,這個我也是有預期的。
至于會不會比通俗孩子更優異,這個我是真沒把握。
因為,在這個宿世界上,每小我都有每小我本身的位置。
而他的位置在哪里,一時半會兒我也看不出來。
而且,在這個多元化的宿世界里,我們其實可以擁有多元化的當作功,和多元化的幸福人生。
我們作為怙恃獨一能做的,就是幫忙他去找到他本身的位置。
不求他超越別人,只但愿他能不竭地超越本身。

—END—
- 發表于 2019-04-05 23:27
- 閱讀 ( 932 )
- 分類:其他類型
你可能感興趣的文章
- 怎樣找到淘寶刪除的訂單 967 瀏覽
- css怎么改變鼠標樣式 1008 瀏覽
- 淘寶購物車刪除的物品想要恢復怎么辦 817 瀏覽
- 騰訊文檔在線編輯使用教程【包含Word和Excel】 9788 瀏覽
- 中國知網怎么查重 789 瀏覽
- 瀏覽器怎么發送post請求 4149 瀏覽
- 通過微信云開發打造免費商城小程序 1204 瀏覽
- 亞馬遜銷量不好必須注意這些細節 748 瀏覽
- 小企業用什么企業郵箱 718 瀏覽
- android手機要下載什么軟件才能打開ai文件 4311 瀏覽
- 手機上怎么打開ai文件 923 瀏覽
- 贈送產品如何計成本 781 瀏覽
- 背英語單詞怎么才能短時間掌握巨量詞匯 1306 瀏覽
- 鍛煉的心里障礙有哪些?如何克服 849 瀏覽
- lol之中使用中單符文法師對線發育的小技巧 810 瀏覽
- 4月份北京周邊旅游攻略 1327 瀏覽
- 如何克服老年鍛煉的六個障礙 1271 瀏覽
- 泰拳怎么在擂臺上對抗,泰拳打法技巧 1268 瀏覽
- 2019清明節旅游攻略 859 瀏覽
- 怎么乘坐火車 766 瀏覽
- 網站分析技巧 1184 瀏覽
- 蘇州旅游好去處,愜意時間游魅力江南 796 瀏覽
- 怎么選擇出行工具 896 瀏覽
- 產業互聯網怎么創業 706 瀏覽
- 到義烏一定要吃的10大美食 2341 瀏覽
- 四明仙山旅游散記中 828 瀏覽
- 面條矢量圖設計 729 瀏覽
- 曼谷王權免稅店攻略 1000 瀏覽
- 韓國公交車怎么坐 2783 瀏覽
- 女生健身的時候出現尿失禁該怎么辦 1388 瀏覽
相關問題
0 條評論
0 篇文章
作家榜 ?
-
 xiaonan123
189 文章
xiaonan123
189 文章
-
 湯依妹兒
97 文章
湯依妹兒
97 文章
-
 luogf229
46 文章
luogf229
46 文章
-
 jy02406749
45 文章
jy02406749
45 文章
-
 小凡
34 文章
小凡
34 文章
-
 Daisy萌
32 文章
Daisy萌
32 文章
-
 我的QQ3117863681
24 文章
我的QQ3117863681
24 文章
-
 華志健
23 文章
華志健
23 文章
推薦文章
- 地震大國,古代日本人是怎樣理解和應對地震的?
- 奇葩后宮里的“雞群效應”
- 地球只是冷了2度,大明王朝卻陷入天崩地裂的浩劫
- 上海人都生活在什么樣的圈子里?
- 我在故宮修房子
- 趙麗穎被爆產后抑郁:你或許不知道,為母則剛有多累
- 為什么說大明實亡于綠化?
- 來武漢一趟,還你一個崩潰假期
- 快手怎么使用魔法表情
- 微信朋友圈怎么看全文 微信朋友圈全文展開方法
- 微信消息怎么設置通知不顯示詳細內容
- esayuiinput如何加單擊事件
- js圖片轉base64方法
- 怎樣在線預約辦理公積金業務
- 澳洲U網的申購版塊怎么用
- excel使用技巧:如何將數據復制到多個工作表
- 如何用AE快速的制作出文字逐字顯現動畫
- 小紅圈如何一鍵導入其他平臺的付費用戶
- 如何注冊電子郵箱賬號,教你創建email郵箱賬號
- 2019年公司車輛怎么注冊滴滴,教程詳細步驟
- 如何辦理 QQ音樂暢聽流量包
- 微信如何記筆記
- 手機WPS Office文檔怎么截長圖
- 華為手機怎么設置應用后臺運行
- 如何使用類成員的函數指針
- 微信最大可以傳多大文件
- winform如何將一個網頁嵌入到窗體中展示
- 網易uu怎么邀請好友
- 微信公眾平臺如何快速增粉
- AE中繼器如何繪制轉場小動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