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歲男孩跳橋身亡,請不要再「殺人誅心」了
 若何對待上海17歲男孩被母親攻訐賭氣跳橋身亡,怙恃與后代應該如何溝通?
若何對待上海17歲男孩被母親攻訐賭氣跳橋身亡,怙恃與后代應該如何溝通?
 李松蔚,通俗的心理學工作者
李松蔚,通俗的心理學工作者
上海17歲男孩被母親攻訐后跳橋,這幾天會商得很熱。也有良多人連結緘默。緘默的人值得我尊敬。別人家發生了這種事,在這個時候,說什么都有點攻其不備的味道。可是看了幾天伴侶圈,我也不由得了,有些話欠好聽,可長短說不成。
言語如刀,有些公號似乎也在批判這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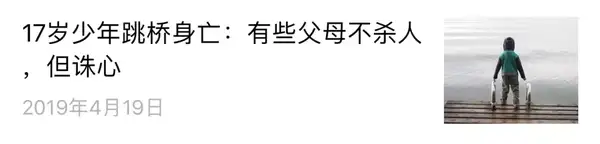
其行文卻在做同樣的事:不殺人,但誅心。
我很是理解,大師切磋這件事的起點很好。都但愿從這件事吸收教訓,避免近似的悲劇再發生。大師試圖警告那個母親,以及千萬萬萬的怙恃:你的說話會給孩子造當作多大危險,孩子出事,都怪你沒做好。但這種出于善意的會商,可能會釀成對這個母親的二次危險,甚至言語暴力。
假設,純粹只是假設,這個母親萬念俱灰走上了絕路呢?介入會商的人會怎么想?
好心說出的話,未必導致好的成果。
一方面,這是別人家的事。網友再怎么厲害,也不克不及經由過程網上的幾句傳言,十幾秒的視頻,就變身當作福爾摩斯,一眼看破別人的家庭關系迷局。——良多網友言之鑿鑿:「我小時辰被怙恃錯怪過,那種感受真的讓人想死!」是的,這話我也贊成。但被錯怪就是這件事的獨一原因嗎?被錯怪的孩子良多,為什么是他不幸走上了絕路?會不會有此外隱情?我不知道,我們其實都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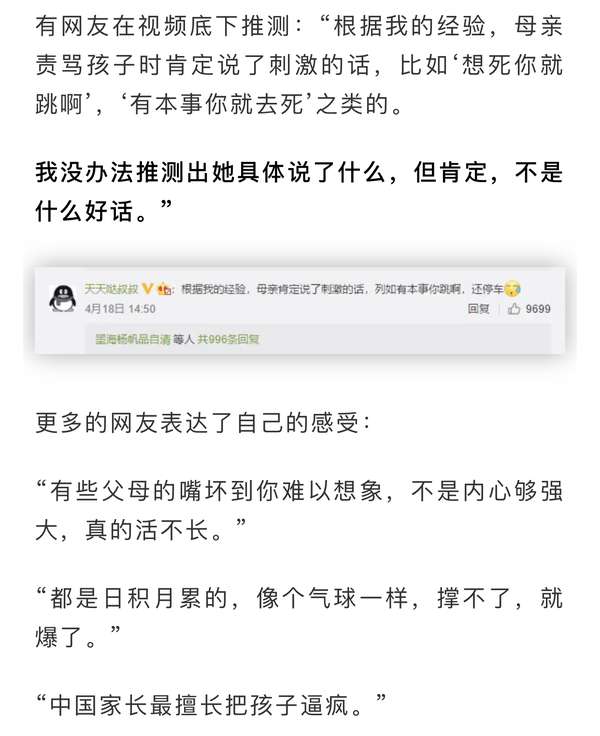
另一方面,若是非要對著這個母親說「都怪你對孩子不信賴,你該對他多一點撐持和理解……」,也有事理。但措辭的人本身就違反了這個事理。面臨不幸,若是只想找一個做錯事的人,對ta施以「都怪你」的訓斥,用一種不容置辯的,訓斥的語氣把不幸歸因給ta,那證實我們并沒有從這件事里吸收任何教訓。因為這個所犯的「錯」,恰是責罵孩子,把他當當作跟同窗發生矛盾的過錯方。我們看待這個母親的體例,跟她的行為有什么區別?
都是把受害者當當作過錯方,橫加求全譴責。
所以,請良多心理學者、自媒體大V、感情專家,出于善意而介入會商的網友,放過這家人吧。這件事若是有兇手,兇手是一個不雅念。一種非黑即白的,別人都必需按「我認為對的體例」行事的二元對立思維。幾十年前,合理情感療法的創始人Ellis把它定名為「絕對化思維」,認為是一種對人有極大危險的信念。直到此刻,它還在潛移默化地影響每一小我。我們還在熱衷于爭執宿世界上有獨一的真理,我的設法是對的,跟我分歧都是錯的。
準確的你,很可能也受過它的影響。
你可能不高興,籌算罵我不知所云,身為一個家庭咨詢師,這一回居然站在怙恃的立場上「洗地」。那我先認個錯好欠好?我說得必定不合錯誤,真的。我們就可以心平氣和一點,坐下來想想:適才我們是不是都有一點絕對化思維?
每小我都可能是這個不雅念的受害者。
此刻我們分開這家人,講點此外。
這件事發生之后,有幾個媒體想采訪我。此中有一個媒體標的目的我供給了一段資料,是知乎一位網友講本身小時辰的履歷。大意是他跟怙恃吵大架,很委屈,這時辰他看到報紙上說,有個孩子跟怙恃爭吵,跳樓自殺了。他就給父親看這段新聞,沒想到父親完全不吃這一套,還問你是什么意思。當然了,孩子愈發大肆咆哮。——后來父親詮釋,說這是因為不想讓孩子拿死來要挾本身。記者從這篇帖子里得出一個結論說,今世怙恃有很強的節制欲,但愿我講一下應該怎么解決。
我的回覆呢,后來可能被刪失落了。我說這事沒那么絕對,若是必然要歸結為「節制欲」的話,我感覺這個孩子節制欲也很強,他也很強烈地想讓怙恃按他的要求行事。當然我理解這一段為什么會刪。是我沒說好,所以我再從頭說一下。
我們在人際關系,尤其是親密關系中,有時會有一種暴怒。這種暴怒甚至會讓人想以「撲滅本身」作為報復。它的原由經常是對方的行為不合適我們的等候,同時以這種句式作為典型的思維:「若是他沒有做到XXXXX,就申明他不愛我/我是一個沒有價值的人/這段關系是一段無意義的關系……」
節制欲是一個不太善意的詞,讓人聯想到一個作威作福的專制軍閥,換個詞可能好一點,好比不平安感。強烈的節制欲,另一面是強烈的不平安。仿佛要把很大的價值,比生命更重的價值,依靠于另一小我馴服 :「他無論若何都應該知足我,不克不及違抗我!……為此我愿意支出生命!」
很辛勞吧?雙方都辛勞。
這樣的設法,超出必然的強度之后,會讓人不勝重負。而我們往往意識不到疾苦的來歷是我們自身的不雅念。我們會誤覺得:疾苦都來自對方,都是因為他沒有按我的要求來(釀成一個好怙恃/好孩子),才搞得我這么疾苦!
這一來,疾苦就會演變為節制。
節制會激發反節制。舉個例子:怙恃但愿女兒成婚生孩子,女兒沒有這個意愿,這原本只是兩代人分歧的糊口不雅念,吵一吵也就而已。但有時辰會激化當作兩代人空費時日的戰爭,令人切齒的深仇。這里就同時并存著節制和反節制。可能怙恃心中有強烈的執念,女兒「必需」成婚,不成婚不可!強烈到必然水平的時辰,怙恃就起頭用各類手段標的目的女兒施加壓力。同時——這一點尤其主要——女兒心中也有劃一強烈的執念:怙恃不「應該」標的目的我施壓,他們「必需」撐持我,不撐持不可!這種環境下她就會反彈:「你們怎么就不克不及開明一點呢!」
我聽過這樣的例子:后代過年回家,已經聽不得怙恃有一聲嘆氣。一旦怙恃起頭說,在樓下看見誰誰一家帶著小孩,真好,孩子就一聲冷笑:「你們說這種古里古怪的話,又想找不利落索性了是怎么著?」然后氣洶洶摔門而去。
你想找是哪一邊的錯,找得出來嗎?
知乎網友的帖子,就跟這個例子中的景象有點像,兩邊都進退維谷。都在擺脫對方的節制,同時又在節制對方。這種環境下,應該把「過錯方」說當作是這個孩子,仍是他的怙恃呢?都不是。怙恃在心里哀嘆:「孩子怎么這么不講理?」孩子也在心里哀嘆:「怙恃怎么這么不講理?」
主要的并不是誰更「有理」,而是兩邊怎么從這個處境中解脫出來。就像武俠小說里兩小我比拼內力到了膠著時刻,拼下去眼看就是油盡燈枯,但不克不及停手,誰停手誰就死。這時是要去爭論誰對誰錯,誰該為此次比拼負責呢?仍是需要系統性的調整:你撤一點點,他撤一點點,你再撤一點……?
我用了兩小我比拼內力的比方,是想說問題是一個復雜的問題,系統性的悲劇。
這一點,至關主要。
我知道,良多人懶得看這種文章。我們想要一個痛利落索性快的結論,最好就是簡單的一句話:你說吧,你繞來繞去的到底想說什么?若是只能用一句話歸納綜合我的結論,我想說的是:「這個問題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并沒有簡單的結論。」
我知道你不想聽這句話,但我但愿你正視它。
這真的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因為復雜,所以不是隨便一個建議就能解決的,也不是片面某小我改一改,問題就不存在了。你當然也可以這樣假設。作為假設沒有問題:「若是怙恃學會罷休,這件事就不至于發生。」你這樣想,可以。可是再往下呢?「有些人底子就不配做怙恃!」再往下呢?「他們怎么就不克不及放一罷休呢!」再往下,「我要讓怙恃看到他們這樣會逼死孩子!」到最后,「他們太惡劣了!除非孩子死在他們面前,他們才會罷休!」——你發沒發現,你想要解決問題的立場,正在一點點地釀成維持問題的一部門。
所以我的建議是什么呢?要看對誰說。對孩子我會說:「放過怙恃吧,他們就這樣了。」轉過甚也對怙恃說:「接管你的孩子吧,他就這樣了。」
墻頭草,但只能如斯。兩句話必需同時說。這邊柔嫩一點,何處同時柔嫩一點。而不是站到一邊,非要另一邊當場認慫不成,成果只有愈演愈烈。
比來我講系統治療比力多。系統治療的很大一部門案本家兒來自于家庭。我在咨詢中處置過良多家庭的矛盾,有的來訪者做著咨詢,就會嘆著氣說:
「沒法子,他就是這么一小我。」
這句話有點無奈,沮喪,有時還帶著氣末路。但總的來說,聽到這句話我會松一口吻。我認為,說出這句話就是一種當作長。它代表著對「紛歧樣」的接管——不是賞識的接管,不是理解的接管,不是心里安然平靜的接管,只是接管。哪怕這樣也好。有時辰,工作的起色只在于一個不情不肯的接管。
你接管他跟你想要的紛歧樣。他不是你抱負的怙恃或孩子,你也試過改變他,改變得也很有限。你就接管他只能是這樣。你不喜好這樣,但你認了。
那代表著你在心里放過他了。
放過他,也就放過了你本身。
我感覺這就夠了,或者說長短常好了。總體上我是一個灰心本家兒義者。樂不雅一點的等候當然可以更高:不僅要接管他,放過他,你還要愛他,賞識他,反過來他對你也要這樣。你們最好能坐下來飽含密意地溝通,擁抱,息爭……但我總感覺這些想象有點太一廂情愿了。我對一廂情愿的工具往往是警戒的,它意味著我們更難以接管紛歧樣。想象越夸姣,「不合適想象」就越讓人不接管。
所以我們仍是回到實際,先接管。
在那個一廂情愿的宿世界里,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壞的,都有物理宿世界一樣光鮮的法例。抱負的環境或許如斯,應該有一些共識,所謂的普適原則:不克不及許可凌虐,不許可身體的損害……那是我們配合承認的,這些方面可以非黑即白。但家庭系統中還包羅良多復雜的環境,難分對錯的環境。按我的經驗來說,簡單的時辰有70%,我們有同樣的價值不雅,同樣的長短,同樣的原則;復雜的環境至少還有30%——溝通體例啊,崇奉啊,教育理念啊,糊口體例啊。后面這些范疇我就但愿多一點「系統式」的寬容:我們有不合,互相看不慣,但可以先這么共存著。誰也不要過于強烈地非要把對方掰當作本身想的那樣。我但愿大師多這樣想一想。
回到跳橋少年的悲劇,若是要從里面吸收一點教訓,我但愿每小我對本身都多點反思,看看心里深處,有哪些口角分明的求全譴責,其實并不合適?
但我鼓吹這種不雅點,是否也在暗暗地劃分一種準確和錯誤?寫這篇回覆的時辰,我也在反思本身的節制欲,結論是我幾多也有一點。我也但愿更多的人認同這樣的不雅念,若是不認同,我也有點掉望。但最終也只能放下吧,究竟結果有的人就是這樣。
- 發表于 2019-04-24 22:17
- 閱讀 ( 816 )
- 分類:其他類型
你可能感興趣的文章
- 64位Python在Win7怎樣安裝 941 瀏覽
- cdr如何制作巨蟹座圖標 872 瀏覽
- springboot實現在線用戶統計 1388 瀏覽
- 3Dmax如何制作茶蓋碗 894 瀏覽
- Mac如何徹底卸載Adobe Photoshop CC 2019 1950 瀏覽
- 3Dmax可編輯多邊形邊界橋 1216 瀏覽
- 用PPT剪裁音頻 887 瀏覽
- premiere的更改顏色怎么使用 770 瀏覽
- 蘋果Mac版QQ瀏覽器如何保存導出收藏書簽 1378 瀏覽
- SolidWorks simulation模擬入門教程(三) 1109 瀏覽
- premiere的快速色彩校正怎么使用 880 瀏覽
- 如何通過photoshop制作保存*.ico的圖標文件 956 瀏覽
- Excel如何將兩或多單元格內容提取到一個單元格 1632 瀏覽
- PS的高反差保留效果怎么制作 850 瀏覽
- springboot實現HttpSessionLisener監聽器 1504 瀏覽
- PPT中變換字體的大小 966 瀏覽
- 命令查看超級管理員用戶的配置信息 901 瀏覽
- 如何制作室內軟裝設計效果圖 761 瀏覽
- SolidWorks simulation模擬入門教程(一) 1137 瀏覽
- WIN8藍牙怎么打開 1126 瀏覽
- SolidWorks simulation模擬入門教程(二) 977 瀏覽
- word自動編號怎么變成純數字編號 1657 瀏覽
- 如何用任務管理器結束進程 1028 瀏覽
- 電腦windows文件過期了如何檢查更新windows文件 947 瀏覽
- MIUI10充電音效怎么關閉 2032 瀏覽
- 蘋果電腦Mac系統如何刪除卸載MathType 1550 瀏覽
- mac輸入密碼后Sorry try again怎么辦 1254 瀏覽
- 華碩筆記本電腦如何連接手機WLAN熱點 1533 瀏覽
- CAD點擊保存就會有彈框出來解決方法! 968 瀏覽
- win7新建文件夾的快捷鍵是什么 758 瀏覽
相關問題
0 條評論
0 篇文章
作家榜 ?
-
 xiaonan123
189 文章
xiaonan123
189 文章
-
 湯依妹兒
97 文章
湯依妹兒
97 文章
-
 luogf229
46 文章
luogf229
46 文章
-
 jy02406749
45 文章
jy02406749
45 文章
-
 小凡
34 文章
小凡
34 文章
-
 Daisy萌
32 文章
Daisy萌
32 文章
-
 我的QQ3117863681
24 文章
我的QQ3117863681
24 文章
-
 華志健
23 文章
華志健
23 文章
推薦文章
- 微信公眾號如何轉載原創文章!
- word行中的內容怎么左對齊
- 生氣頭像設計
- 上學女孩圖片設計
- 戰艦圖片設計
- 個人簡歷的特長可以寫些什么
- 手機都有哪些掙錢的方法
- 減肥為什么會失敗,原因是什么
- 生活中有哪些食物是不適合長期吃的
- 懷孕期間如何照顧好孕婦
- 肝不好,人體會有什么信號
- 孕婦應該吃什么,不應該吃什么
- 怎么正確吃南瓜
- 常吃什么水果可以豐胸
- “鼠標手”的防治方法
- 康棒蛋白棒減肥心得
- 產后肚子有贅肉、腹部松弛,可能是腹直肌分離了
- 坐著怎么減肥
- 身體免疫力低的幾種跡象
- 高效瘦身時間表
- 懷孕期間如何增強抵抗疾病的能力
- 克服男性睪酮激素缺乏的6種方法
- 春季飲食,如何清潔身體
- 早上應該做些什么運動快速減肥
- 持續疲勞可能的原因有哪些
- 怎樣在wps文字中創建折角形
- 怎樣在白板中繪制并克隆三角形
- 怎樣創建爆炸星形并給它填充顏色和形狀
- 夫妻“冷戰”6招教你迅速緩解雙方矛盾
- 筋膜炎吃什么藥能治好